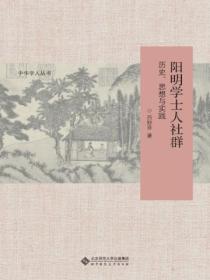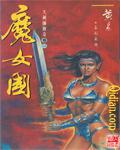一、道统观
儒家道统观所宣称的学术正统性,不仅关系着学术风潮,更与政治权力息息相关。虽然正统所拥有的学术宗主地位和政治势力的背书经常具有学术支配权,但是正统的内容绝非一成不变,在学术和政治复杂的交互作用下,正统的内涵不断地被修正和塑造,透露着学风转移或政治变易的迹象。[1]借着道统观来争取或巩固学术的正统地位,更是儒学在宋代以降的学术、政治舞台上极重要的演出。
道统的观念渊源甚早,而“道统”一词则由朱熹首先使用。[2]从北宋起,道统观已逐渐成为儒学的重要课题,[3]这观念之所以在宋代萌兴,与其说遥承孔孟,毋宁说是承自唐代的韩愈(768—824)。儒学思想在经历六朝至唐代长期衰微不彰之后,韩愈成为重要的儒学发言人,尤其《原道》一文写道:
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4]
韩愈不仅明白打击佛老、宣称儒家的正统地位、更提出道统的系谱,为宋儒兴起的先声。Peter Bol精辟地讨论了韩愈等学者的古文运动和宋代儒学兴起之间的关系,并配合着社会结构的转变,说明程颐的道学如何在王安石(1021—1086)新学派和苏轼(1036—1101)古文学派间逐渐崛起,成为主导宋代人文价值观的主流思想。[5]黄进兴也指出,由于韩愈在道统系谱中着意突出孟子承先启后的重要性,不仅使得道统的接续成为宋儒关切的课题,也使得孟子的地位在宋代大大地提升;事实上,韩愈本人在宋初也受到极大的尊崇,被置于道统传承之一环,直到王安石新学当道时地位才稍降,随着道学兴起,更被请出道统传承之列。[6]程颐在《明道先生墓表》中便以程颢直承孟子之传:
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7]
程颐的道学深刻影响了南宋的道学发展,南宋道学在经过张栻(1133—1180)、吕祖谦、朱熹、陆九渊、陈亮(1143—1194)等人的彼此问学论辩和竞争之后,最后由朱熹集大成,其内涵却也更狭隘地朱学化;道学的地位虽经指控迫害,但终于在理宗淳祐元年(1241)获得朝廷的肯认,从此朱学的地位节节上升,深切影响了元明清的学术发展。[8]朱熹的道学与程颐之学最相近,再益以个人体悟自得,故世以程朱学连称;关于道统观,朱子不是偶尔提及,却是积极塑造,根据张亨的研究,建立道统可说是朱熹一生的志业,而其道统系谱的内容虽大体承继程颐,但积极加入周敦颐,使之成为千百年后直承孟子之传的真儒。[9]朱熹在《近思录》中云:
自唐虞、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道统相传,至于孔子,孔子传之颜、曾,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遂无传焉。……迨于宋朝,人文再辟,则周子唱之,二程子、张子推广之,而圣学复明,道统复续,故备著之。[10]
朱熹以北宋的周敦颐、张载、程颢和程颐承继孟子之传,重续道统之谱。这一个道统系谱也因着宋理宗从祀诏的背书(1241年),而成为官方认可的正统系谱。[11]黄进兴指出,在理宗从祀诏中,朱熹更是灵魂人物,不仅他在《近思录》和《伊洛渊源录》所塑造的道统系谱完全被朝廷采纳,他所受的封爵也比周张诸子高。[12]从此伊洛一派的道学主宰了官方从祀和学术正统的标准。大体而言,从元代到明代朝廷从祀孔庙的规制,均尊崇朱熹伊洛学脉,朱学的内涵及所塑造的道统系谱在学术和政治地位上都高居正统地位。
学者已指出,道统观念的塑造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和排外性,[13]虽然它宣称指涉一绝对的真理,即儒家真道的传统,然而“真道”的意涵由谁赋予?真道的传承者如何决定?我们虽不能完全抹杀提倡者对“道”的真诚信念,但在宣称自己相信的正统的同时,则已实质地涉及了学派间的政治之争。从孟子开始,辟杨墨之流便是论学的重点;韩愈《原道》一文最主要的目的是排斥佛老、提倡儒学;程颐在称扬程颢传孟子不传之学、倡圣学之后,也强调其辨异端、辟邪说的成就;朱熹的伊洛学脉,除了辟佛道之外,更欲在不同儒学派系中,标举道学。在道统系谱中,只有被点名的少数学者被认为是正统圣学的传人,其他的儒者都被摒除在外,因此提出一个道统的系谱,绝不止是学术性的,更具学派间竞争的政治性,而一旦获得朝廷拥护,则又进一步以官学的政治力享有学术霸权。这也就是朱学及其道统观在王阳明时代的情形。王阳明既然公开地批判朱学、宣称自己致良知之学才是儒学真道的传承,对于朱熹所提出的道统系谱,他的态度如何?道统观与其宣称自己学说的正统地位又有何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