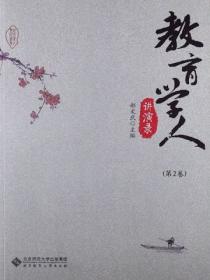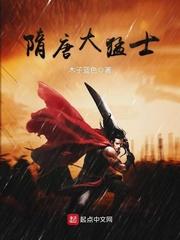三、当前教育研究方法论重点探讨的问题
第三点是当前教育研究方法论应探讨的问题,或者应该重点探讨的问题。那么既然教育研究方法论如此重要,而我国教育研究在方法论这个层次上也非常需要人们认真地思索,因此,我认为当前我们重点探讨的问题应该有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重新认识形而上学的方法论价值。那么这是个什么问题呢?从刚才方法论体系来看,实际上就是一个如何重新认识哲学方法论价值的问题。可以说,自19世纪以来,在很大的程度上,由于科学的发展和科学方法的盛行导致了人们有意无意地排斥形而上学的价值。即使哲学本身,也有人主张具体的形而上学,比如说实证主义。这样就导致19世纪以后人们对形而上学在研究方法上的价值认识不清,当然更导致了科学方法的泛滥。它使得很多人认为形而上学不就是思考、假定、抽象和在大脑里面做文章吗?认为这种研究方法是严重脱离实际的,所以使形而上学的研究价值每况愈下,而这一种认识在当前的我国同样存在。对这种现象包括19世纪以来对形而上学拒斥的现象,我是不以为然的。为什么呢?形而上学作为研究方法的真正价值,还没有被我们当代人充分认识到。在我看来,历史上留下来的经典包括教育经典,绝大多数都是形而上学的作品。康德的“三大批判”,没经过任何实验,在他12平方米的斗室里,康德把整个世界装进他的心中,写下了“三大批判”的名著,可以说是名垂青史,没有任何人能否认,至今也没有多少人能够超越。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更是在思维世界里建构起了一个强大丰富的精神王国。谁能否认这些形而上学作品的价值?没有任何人能够否认。倒是相反,那些所谓以科学,以实验、调查、测量为特征的作品,随着历史的演进往往成为历史的尘渣。很多人意识不到这一点。而我要说的是,我们的教育研究缺少的不是实验实证的许多具体数据,恰恰是缺乏形而上学的巨人。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教育理论落后,不是实验落后,不是数据落后,不是统计手段和方法的落后,是形而上学落后,教育研究中形而上学的精品几乎是空白。更有甚者,以所谓理论的空洞抽象、以所谓理论的空想、假定为借口来否认理论研究的价值。我认为这在当前的中国是一种非常不正的学风。这里少了一种什么?少了一种胸怀。科学方法有科学方法自身的价值,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不能因科学方法价值的彰显而否定形而上学方法的价值。作为研究者就要有一种研究的胸怀和境界。讲到这个地方,我有些感慨,导致中国目前在某种意义上轻视理论思维,轻视理论探讨,轻视形而上学的探索,它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与我们长期以来信奉所谓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个教条是有很大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当然要结合,这是没有什么错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忽视了另一个结合——实践也要和理论相结合,可是我们却抛弃了后者。这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想法或者一种误解,认为理论只有同实践来结合,理论才有价值。其实,真正的理论可以不与实践相结合,因为它自己有它自身独特的思维价值。有多少人认识到这一点?没有。所以这导致我国长期以来搞理论的人往往是灰溜溜的,往往结合就是迎合,而搞实践的人在任何时候都是老大。我认为这种认识是不对的,用我们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含义来讲,这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的方式。注意,我说的是用传统的形而上学,即孤立、静止、片面地看问题。我认为只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不讲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就是孤立、静止、片面地看问题。所以我的观点非常明确——今天我们要重新认识形而上学的价值。那么什么是形而上学?它实际上就是指一个人在思维世界建构起一种的抽象理论,推导出一种人的形象的假定,以此去认定教育的本质属性。它不需要任何实验,更不需要所谓的观察,而只是思考、推理、判断和抽象。
第二,对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做指导,今天我们要深入研究。我的意思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指导教育研究,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另一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的典型表现就是中国的传统的研究方法,要么是“六经注我”,要么是“我注六经”。我们今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做指导,无非就是这两种方式。我认为这两种方式都有问题。所谓“六经注我”,那就是观点可能是你的,但是你自己论述这个问题缺乏底气,缺乏力度,就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作品当中寻找一些只言片语来解释你的观点,这就像你说话好像没有分量,就找经典作家的原著原话来支撑。“我注六经”,比如说把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当中已经有的结论搬过来,然后自己再去做一番无病呻吟的论述。这两种做法都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做指导,这种做法无益于教育研究的发展。我认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最核心的有三条:第一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批判精神。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理论上有很大建树的精神之源。而我们在这一点上应该说学习得很不够,当代中国谈不上什么学派,更谈不上有什么学术派别之间的争议,更多的是理论上的一团和气,更多的是对政策方针的注解或者诠释,缺少独立的批判精神。第二是理论思维。就是我们国家今天的教育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与当年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比,理论思维能力退化。如果有兴趣、有时间,请大家读一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在他们的著作当中渗透着一种深刻的理论洞察力,我认为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难以达到的。在座的有不少研究生,可以读一读马克思26岁时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26岁的年龄写下一部如此成熟的学术著作,可以说其理论思维能力所达到的水平是很多同龄人达不到的。学马克思,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多少人能够用这样的观点去看问题。相反,今天很多人认为理论思维要不要都无所谓,只要我们调查、只要我们观察、只要我们统计分析了,我们同样可以进行研究。那我告诉你,鸡有的时候比老鹰飞的还要高,但是鸡永远也飞不到老鹰所达到的高度。我不知道我这句话大家理解没有,就是说所谓科学研究,所谓定量研究,偶尔可能横行一时,霸道一时,但是在理论上达到的高度永远不及哲学和理论思维。什么叫方法论,我认为这就是对方法论问题的思考。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主要的特点,第一是批判思维,第二是理论思维,第三是实践思维。这一点我刚才谈到了。今天很多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如果用实践唯物主义来解释,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人类在认识、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当中,不仅改造着客观世界,更要建构主观世界。我前天在这里召开的教育哲学高层论坛上就讲到,实践是一个双向建构,而我们以前只是把它理解成为一个单向的,即我改造客观世界。但马克思讲,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当中,也在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这就是马克思自己所说的,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看作并被理解为变革的实践。这里我想说的就是要提升我们广大的实践工作者的理论思维能力。试问我国千百万教师,有几位教师在实践中实现了对自己的改造,也就是实现了对自我理论水平的提升?几乎没有。所以我们国家的教师,在很大程度上是盲目的实践者,或者是被动的实践者,或者是方针政策的简单执行者,而不是主动的探索者,更不是通过实践使自己提高,然后再用提高了的思维能力去驾驭实践。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灵魂在今天被我们完全遗忘了。教育实践工作者是这样,教育理论工作者也是这样。所以我在给我的学生讲课时谈道,教育研究者必须打好三大基础,否则你这个研究没有办法继续下去。这三大基础分别是哲学基础、外语基础和实践基础。研究教育的人,不懂中小学教育实践,即使有抽象理论思维,可能也与实践离得太远,无法关照实践。所以我这里讲的第三点,即批判思维、理论思维、实践思维,强调的是实践工作者要实现双向改造,既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使自身不断得到发展。
这里附带说一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从当代世界形势来看,特别是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来看,已经非常丰富了。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渗透在当代西方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各个领域。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像很多不太懂马克思主义的人所理解的那样,认为马克思主义今天不行了,没有生命力了。可以这样说,如果不了解马克思主义,那么你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就没有学术上的发言权。我这里说的意思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即使在当代学术界,其生命力之旺盛是很多对马克思主义产生误解的人所不了解的。
第三,进一步探讨国外教育理论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以期从方法论的角度为我们研究教育提供参考。这里主要讲的是我们研究教育,特别是研究国外的教育,往往是研究、借鉴某种具体的理论较多,但是对于这种理论背后的方法论研究太少,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探讨国外教育发展背后的方法论取得成功的原因在哪里。在西方教育思想史演变的过程中,被我们称为教育思想家的很多人,他们并不是就教育来论教育,恰恰相反,很多人从其他学科的角度来思考教育,从而取得了重大进展。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方法论问题。所以我们教育研究者要反思自己的方法论。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夸美纽斯在大学里学的是神学和哲学,当时的大学没有什么教育学。后来夸美纽斯却建构了我们所说的经典教育学。赫尔巴特是教哲学的,可是他对教育学做出的贡献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我们很多人知道福禄贝尔,他写了教育名著《人的教育》,而他大学里念的是化学,在他的自传里曾写过这样一句话:化学的结合力使我神魂颠倒。可见,他非常热爱化学这门学科,但是最后他转而研究教育。杜威是研究心理学出身的,后来由心理学转为哲学,再来研究教育。而皮亚杰更是走了一个大圈子,皮亚杰是研究生物学起家的,由生物学到医学,由医学到心理学,由心理学到哲学,最后再转向教育学,所以皮亚杰有个著名的论断,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差不多半个世纪,教育学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所以我想,研究思考国外的教育理论,就应该看看别人研究教育的方法论究竟是什么,这有利于我们摆脱“就教育论教育”这种思维模式,也有利于我们从其他学科借鉴某种有用的方法来改造我们的教育研究。这里的研究就有一个研究教育学发展史的问题,如果一个教育研究者对理论发展的历史缺乏系统透彻地了解,他就很难有突破性的进展。可以说史学是任何一个研究者的基础。至于当代国外教育理论的很多新进展,实际上也是综合运用了许多新的方法。比如说范梅南的教育学,很多老师同学都非常熟悉,其教育学是一种现象学的教育学,运用现象学的还原方法研究教育,从而获得了很多新的启发。而弗莱雷提出了解放教育学,解放教育学之所以在西方世界近30年来非常流行,正是得益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对当代世界特别是国际关系的理解,尤其是对第三世界教育的洞察,由此才提出了震撼力非常强的解放教育学。对于这些理论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我国教育学为什么不能有新的进展,我认为应该研究这个方面的问题。
第四,就是对我国目前使用的教育研究方法应该进行哲学层次上的反思,即方法论上的反思。分析这些方法的利弊,以便使我们在方法论的选择上扬长避短,仅举一例来说明。比如实验的方法,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教育研究的显性方法就是实验法。曾经有人做过统计,我国大大小小的教育实验以及以实验冠名的研究多达一万多种。可是经过30年所谓教育实验,我们成功的教育研究成果在什么地方?放眼望去,一片荒芜。这与我们盲目地运用实验方法有很大关系,更有甚者,以教育实验为名,最后是沽名钓誉,拉大旗作虎皮,完全是走过场,流于形式。究竟现在用的方法有多大价值,很少有人直面这种现实。然而更有人把通过实验得来的一点点成果无限夸大,盲目吹嘘。我曾经就见到《教育研究》发过这样一篇文章,这个实验研究是研究小学低年级的复式教学。复式教学大家都知道,一二三年级的学生在一个班上上课,一个老师同时面对几个年级的学生。他对该实验的研究结论,吹嘘到此实验为中国21世纪的基础教育探索出了一条新路。我认为这是学风问题。科学最讲究严谨,最讲事实,可是我们很多运用所谓科学方法的人,却违背了科学方法所要求的常识。我们对现在使用的这些方法,很少有人进行具体的探讨。
第五,我主张重视对元教育学的探讨。反思教育理论和教育研究,提升教育研究的自我意识。这个问题我不展开说了,可以说我们国家元教育学研究还只是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在西方20世纪70年代以后,很多学者致力于元教育学的研究,并提出了很多方法论性质的新观点。比如说德国教育家布雷岑卡,很多人都知道,他关于元教育学的研究有一个成果是,教育学理论的三大构成是教育哲学、教育科学和实践教育学。这三大构成实际上是对教育学进行元研究以后,认为教育理论的结构应该是这三大部分。而我们国家的元教育学研究起步比较晚,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引起人们的重视。元教育学简单地讲就是对教育学本身进行研究,研究教育学的结构,研究教育学的逻辑起点,研究教育学的性质,研究教育学的历史发展,研究教育学的社会功能等,就是把教育学本身作为一个对象,我们平时的教育研究对象是教育现象,那么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理论。那么我认为要在这一个方面展开研究,以提升教育学的自我意识,更达到提高教育研究者的自我意识的目的。
第六,教育哲学应该成为探讨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学科。研究教育与教育方法论更多的是从教育哲学这个层面去研究。在西方哲学中它有两种含义:一是作为动词的哲学,二是作为名词的哲学。作为名词的哲学由来已久,而作为动词的哲学应该是现代哲学,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哲学所具有的含义。那么教育哲学意味着什么?对于教育进行哲学研究,也是用哲学的思维方式来思考教育,这其中就包含着对教育研究方法论进行思考。比如说我这里讲到的实际上是站在教育哲学的角度来思考教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所以在我国,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划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研究教育中的问题,但是研究的方法是从哲学的角度进行的;二是研究教育研究方法论,站在哲学的角度,用哲学的眼光对教育研究方法进行甄别、批判和选择。所以说,我国在教育研究方法论的研究上还有待加强,这是我国目前教育哲学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我今天讲的更多的就是这个环节——用哲学的眼光对教育研究方法论进行一些反思。
以上就是我围绕对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思考,跟大家谈这几个方面,不一定妥当,主要是个人见解,目的是学术交流。谢谢大家!
提问互动
李国庆:
王老师刚才给我们做了一个简短但又非常扎实和厚重的报告,他主要论及3个问题。我们在座的老师或者同学可以认真思考一下,这些确实都是我们在教育研究和实践中经常涉及的问题。比如说他关于方法论概念的论述,讲到任何理论的创新都必须有一个方法论的创新,如果没有方法论的创新,那么任何理论创新都是不可能的。他还谈到了华东师范大学的叶澜老师也论证了这个观点。另外,他还谈到关于教育研究方法从横向、纵向的划分,比如说纵向的三个层次:哲学层次、方法论层次和具体的方法层次。从横向方面,他阐述了哲学的、科学的和历史的方法。讲得非常清晰,也非常厚重。尤其是在第三个问题中谈到当前我们国家在教育研究方法论的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其中的一些观点确实值得我们同学和老师进一步思考。尽管这些观点还值得进一步研究,但是应该引起思考。比如说如何看待形而上学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都把形而上学作为一种批判的对象,认为它就是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看问题,是不是这样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没有理论思维,任何科学的东西怎么能够确立?没有理论的指导,怎么去实践?所以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很早就讲过这样一句名言:“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高峰,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思维”。形而上的问题就是强调理论思维,刚才王老师也谈到,马克思26岁就能完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那样高度的文章,他后来写作《资本论》、分析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这种高度的理论思维,他能成功吗?所以说对于这个形而上学的问题的正确的评价,也确实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还有关于我们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做指导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后应该注意的问题。他谈到了长期以来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这样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吗?这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当然也提到很多其他问题。让我们对王坤庆教授为我们教育学院做的精彩报告表示衷心的感谢。(掌声)尽管时间比较紧张,按照我们报告的惯例,我们还要进行一些互动。那么下面就王老师报告中提到的相关问题同学们还有什么需要请教的请举手提问,王坤庆老师将给予回答。
问1:您说现在研究教育问题要有哲学思维,那么基础教育老师应该怎样建构他的哲学基础和哲学思维呢?谢谢。
王坤庆:你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个问题与我本次在教育哲学高层论坛上的发言是直接相关的,我的发言就是“教师专业化的境界:建构教师个人的教育哲学”。实际上我的观点就是作为一个基础教育中的普通教师,我们今天讲专业化,更多的是讲老师对教材的理解,对教法的选用,对技能技巧的熟练以及对学生如何关怀,如何理解,很少上升到教师要形成个人教育哲学这种境界。具体来讲,我们今天的教师专业化要引导教师,包括我刚才讲的要认同理论,亲近理论,向往理论。而今天很多教师对理论往往是望而生畏的,这就更谈不上去形成教育哲学了。所以我的主张是,教师专业化建构教师个人的教育哲学有四条途径。一是要读书。教师什么时候把读书看成是自己的日常生活方式,那么我认为他们的素质就提高了。但是据我了解,今天的普通教师读书太少,很多教师常年不读书。二就是要培训。今天很多教师的培训只是一种形式,我认为这种培训效果不好。特别是很多组织培训、管理培训的人,他自身素质就不是很高,很难设计出一种提升教师理论水平的培训。以我所见到的××省为例,管理教师培训的,无论是教育厅的干部还是教育培训的相关管理部门,自身对教育的认识和理解就非常有限,怎么能够去提升教师的这种水平呢?所以要改变这个情况。三是实践。我刚才讲到教师的实践不是盲目的,不仅仅是一个干活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反身建构、主动建构,在实践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提升自己。在这一点上,波兰尼的主观知识论或默会知识论,就是针对教师如何提炼属于自己的实践知识、个人知识的理论。这种实践知识和个人知识的积累就有助于教师教育哲学思维的形成。我认为教师如果是在这几个方面注意提升自己,作为一个自觉的教育工作者,作为一个有教育哲学信念的教育工作者,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的。这就是我自己的一点看法。谢谢大家。
问2:王老师,谢谢您深刻与厚重的讲演。其实我还是想借着师兄刚才的那个问题。就是刚才当您讲到我们的教师由于缺少理论思考而在实践的低水平上重复或者盲目的徘徊的时候,我的感觉首先是很激动,因为我也长期思考这个问题。我以前思考在教师职前培养这一段如何提高教师的教育理论素养。刚才您谈到在之后我们作为教师应该从哪些方面去做。那么我想就是在对教师进行职前培养这一段,您有什么好的建议?谢谢您。
王坤庆:这个问题应该说是问到了我的本行。刚才李教授(李师兄)介绍了我是华中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而华中师范大学跟陕西师范大学一样,是一所以教师教育为主体或者是教师教育特色鲜明的部属师范大学。所以自从免费师范生进来以后,我们在这方面采取了不少措施。主要措施大概有三点:第一点就是扩大原有教师教育中教育类课程的比例,特别是学分比例。我们算了一下,原来传统的师范教育模式当中教师教育类课程的学分在我们学校只有11个学分,无非就是老三论,教育学、心理学、教材教法,再加上一个教育实习,一共11个学分。而现在学校教师教育类课程的比例达到了28个学分,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了。也就是说重视教师教育类课程的开设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强调,大学生在校4年中解决所有的教育问题,这是不可能的,那么提高学生的教育技能技巧,那是有可能的,但不一定完全做得到。因为技能技巧是实践的过程,是个练习的过程,没有经过实际的锻炼,仅靠师范院校的4年,很难在这个方面有所作为。所以我们的观点就是师范生达到6个字,叫做懂教、爱教、会教。这是理想的目标。我们的信念是什么呢?在这4年当中,要让学生懂教,那就是提升学生的教育理论水平,尽量使学生爱教育,爱教师职业,在4年中对学生进行职业道德的教育。会教,我们在这个方面有一些措施,但在这个方面不像有一些,特别是原来的中等师范院校或者是师范专科学校强调的那么厉害。我们强**师掌握基本技能,那就是三字一画。其他的技能是在工作以后完成的。也就是说在这6个字当中,一定要达到懂教,通过教育理论的学习,让学生懂得什么是教育,主要是理论。爱教,我们要培养学生热爱教育事业,不一定完全达到,但是师范生应该有这个素养。尽量让学生做到会教,也就是突出了教育理论的重要地位。对于技能的培养,不像有些师范专科学校或者是原来的中等师范院校把技能强调的特别厉害,我们是部属师范大学,培养的目标是未来教育家,这是温家宝总理的号召。我们没有见到过哪个老师由于他娴熟的教育技能、技巧而成为教育家,成为教育家的人一定是有教育思想的人。我们的师范教育的目标也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么第三点,在4年的培养当中,我们也比较关注学生的实践技能等各方面的培养,并不完全放弃。但是我们只是关注学生的基本技能,而不是关注学生的、班主任技巧、组织班会、辅导学生的心理等,这些太多的具体技巧,我们不太关注,而更关注一个师范生的基本素养。粉笔字一写,别人一看受过训练,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类似这种基本的东西是基本技能,而不是纯粹把学生当成工匠来培养,这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我就讲这么三点,谢谢。(掌声)
问3:王老师,您好!我一直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我国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从事教育问题研究的人数恐怕是世界上最多的。然而迄今为止,我国在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方面,没有一位在世界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大家。您认为是方法论出了问题还是政治体制存在问题?
王坤庆:可能原因还是多方面的,并不是哪一个方面的原因。我也承认,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在世界上被认同的中国的当代教育家,确实不太多,几乎没有。这是个事实。那是什么原因呢,我想还是多方面的。这个反正是学术交流,我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了,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有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指导作用的理解发生了偏差,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就是我们的教育理论,我们的教育研究不能提出新观点,任何观点都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引导之下。我以为在这个方面还是出了点问题。人们片面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而我刚才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在指导教育方面有三点:一是批判精神几乎没有;二是理论思维也不能说没有,但是人们对这方面非常不关注,甚至理论包括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压迫的,在这种背景下,还有什么理论可言呢?三是实践思维。主动的建构、主动的提出这个方面做得不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是我的看法,与我们国家曾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解读不是那么准确也有关系。这点在哲学界早已有所议论。我国哲学界从80年代开始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在已经进展很深了。其中比较典型的有两个内容:一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是否有价值论这个问题探讨的很多,我想搞教育哲学或者教育基本理论,有人对哲学有所了解的话,在8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国家的哲学界率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构成上打开突破口,认为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的重要内容,但是我们国家以前都没有这个内容,那么这种状况是如何产生的?是从苏联借鉴过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苏联人认为,价值哲学是资产阶级哲学的专利品,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价值论。二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以前我们国家把马克思主义概括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或者是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四大观点。前者没有价值论,后者没有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在其中的重要地位。这导致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所谓的科学,我这里附带地说一下,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解释成为科学的这种观点在我国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哲学就是哲学,哲学不可能是科学。可是我们国家往往把哲学解释成为科学,这是受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把一切东西都往科学这个口袋里面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装进了科学,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解。什么是科学?科学就是真,真是能够验证的,能够证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就是价值,是信念。这就是哲学。哲学是价值,是信念。我们连这个基本问题都混淆了,所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理解是有偏差的。这导致我们只能按照那种机械的、本本的马克思主义行事。第三个原因,我认为在我们国家,不能叫政治体制吧,我不太同意这个看法,我认为与我们的政治背景是有关系的。前30年主要是一种政治主导的背景,后30年主要是一种经济主导的背景。在这两大主导背景下,我们的研究很少能逃脱那种背景或者是远离那种背景,就像我刚才讲到的那种独立思考、独立探讨的东西。这样就很难产生与我们的时代相差很远的那种新的理论。更多的是一种政策性的、现实性操作性的,很难有真正的理论。用我的话来讲,真正的理论应超越它的时代至少50年。所以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而这种情况我也认同,这就是我的回答,谢谢大家。
问4:感谢王老师的精彩演讲。从王老师的演讲中,我听出王老师好像比较提倡理论研究,但是我这里有一点不明白,就是您说的理论不与实践相结合,也可以有它自身的价值,那么这个价值怎么体现,它体现在哪里?我想请教您一下。谢谢!
王坤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可能有不同的理解。那么我讲的这个就是刚才李教授讲的,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种假设,或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理论工作者的追求。与实践相结合,我们不能机械地理解成为就是与教师的教书相结合或者是怎么样。那就是说理论在很多时候就是一种思维世界建构起来的逻辑体系。那么这种逻辑体系也许在当代在当前人们认为它太抽象,太空洞,不切实际,那么我就说它可以与实践不相结合,我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这个理论说不定在未来某个时期,在历史发展到了相应的时代,它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不是表面上所看到的,我一提出来它就要运用到实践当中。所以我说的真正的理论,如果我们把它运用得比较好或者是探索得比较好的话,它是一种永恒意义上的东西。比如说历史上很多经典,今天看起来它之所以仍有道理,就是因为它寻求的都是普遍的原理,而不是具体的历史时代要解决的某一个具体的问题,那样的理论随着历史的发展就会被淘汰。我们追求的应该是这样一种理论,不与现在的、这个时候的实践相结合,但并不意味着它对实践毫无价值。我想我的解释应该是这样的。谢谢!
李国庆:刚才这个同学提的问题还是有一些普遍性的,理论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王老师刚才讲的,像现在咱们已经建立了很多理论,比如天文学理论,它不是靠实践观察,也不是从实验来的,它是由科学家从理论上论证出来的,那么最后再实践证明这个理论恰恰是正确的,它的价值就在这儿。爱因斯坦很早就谈到要培养直觉思维,什么叫直觉思维?不是由过去的实验分析得出的结论,他的很多理论经过理论推导,从直觉上认为哪个理论是正确的,有坚实的理论基础,那么最后,经过若干年甚至于几十年,论证他直觉地从理论推导出的思维是正确的,它的价值就在这里。它起一个先导作用,而且它的科学价值非常高。我想它的理论意义是很大的。
问5:谢谢尊敬的王老师。我的问题始于6月26号早晨您的精彩报告,就是建构教师个人的教育哲学,这让我对教师的定位提到了一个很高的认识层次,拓展了我的教育视角。我的问题就是,教师要建构自己的教育哲学,其中包括发展观、学生观、质量观和知识观,我非常赞同,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方面。我的问题就是,在当前的教育实践当中,教师的这四大观受到了很多影响,包括政府,包括社会的认可,包括学校的管理,包括教师自己的定位,那么在教育实践当中,在这几个方面的影响下,教师如何定位?如何把四大观发展起来建构自己的教育哲学?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谢谢王老师!
王坤庆:你的观点我理解了。这个问题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在短时间内我很难按照你希望的那样回答,这是个难题。我想说的大概就这么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随着教师本身素质的提高,他对一些基本的理论的认识应该是做得到的。比如说学生观,师生之间是平等的,看到学生身上的能动性、主动性,会更多地调动学生、相信学生、尊重学生。这个我觉得从理论的认识上应该说还是做得到的。发展观包括我前面讲的知识观,现代的所谓建构主义也好,后现代主义也好,从这个知识层面上,通过一些培训,我认为这个还是做得到的。通过某种方式就是可以使教师的认识达到这几种观所需要的基本理论上的要求。第二个你可能更多地强**师把这些认识转化为自己的实践,而现在的教师更多的是依据政策,依据上面的高考“指挥棒”,或依据社会公众舆论的导向,因此教师没办法施展这些观。那么我觉得这个还是应该具体分析。作为一个创造性的教师,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去实践自己的这些观念的,我不想讲多了。就像我刚才说的,教师作为一个创造者,没有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没有对自己的职业有更高的追求。我举一个美国老师的例子,美国的一个小学4年级的班主任老师要接收一个从国外来的且从未见过面的插班生,美国是大国,美国人唯我独尊。但在这个学生报到的前一天,这个班主任就给他写了一封亲笔信。信的内容有两个意思:第一,对这个小朋友的到来表示欢迎;第二,相信这个小朋友会与他们这个班一起度过一个激动人心的学期。美国的一个普通的班主任老师对学生的爱能够做到这一步,我认为是教师把自己的职业理想和情怀渗透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了。我们中国的教师,大家都是做老师的,或者是有过当学生的经历,你认为你的老师对一个还没见面的插班生,能有如此关爱的情怀吗?几乎是没有的。我们说教师有能动性,教师有自己的观念,完全有空间表现。可是我们的老师做不到。那天也有人提到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老师做不到?我们的老师境界太低,把教书只当成谋生手段,把教书只当成是完成任务的过程,把教书只当成自己的职业,没有当成人生价值实现的舞台。这就是我的回答,谢谢你。
(参加本文整理的有,博士后:周先进,博士生:郭辉 张京京 硕士生:杨锐 曹建芳 王晓晶 闫苗 王登峰)